-
股票如何申请杠杆 哲学点亮语文课堂如何让教学通向生命的觉解?_庄子_死亡_经典
发布日期:2025-08-02 21:14 点击次数:10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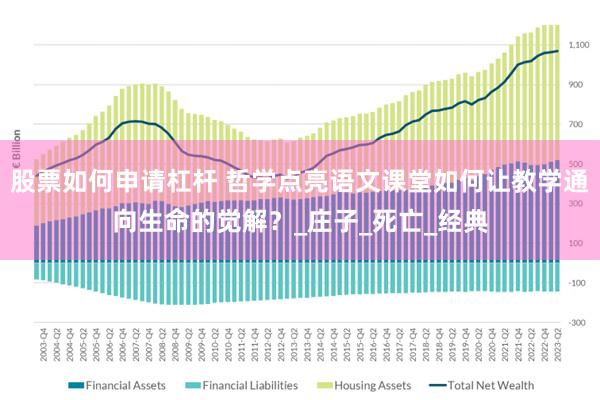
说起来似乎有一点不务正业,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股票如何申请杠杆,我更痴迷于哲学阅读,更喜欢用哲学的眼光去审视我的语文教学。这样的阅读志趣和阅读视角也直接影响到了我的语文课堂教学。我习惯于寻绎吟玩文本的哲学意蕴,习惯于把哲学的理性与反思带进语文课堂,习惯于不以最终结论为旨归的哲学式追问。于我而言,与其说是用哲学的望远镜在看语文的风景,不如说我是站在语文的大地之上凝视哲学的天空。
我与哲学的结缘源于一次小时候参加邻人亡故后的葬礼活动。破孝日傍晚,道士摇铃念咒,众人紧随其后,执香绕棺。墙壁上悬挂的是巍峨耸立的森罗殿图,十殿阎罗伟岸庄严,寒气袭人。那一刻,我突然想:亡灵真的可以超度吗?人死以后真的还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生命真的可以轮回吗?
这应该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哲学发问。若干年后,当读到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时,我似乎对生死这样的大问题才有了茅塞顿开的领悟。索甲仁波切说:“我们的存在就像秋天的云那么短暂,看着众生的生死就像看着舞步,生命时光就像空中雷电,就像激流冲下山脊,匆匆流逝。在一切足迹中,大象的足迹最为尊贵;在一切正念禅中,念死最为尊贵。”所以,在教授《兰亭集序》时,对于王羲之“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的感叹,我以为这些话正好与之构成互文见义的关联。人们对“死”的恐惧无外乎把“死”看成了“生”的另类而忌惮和忌讳,于是怕死,怕死也就拒绝思考“死”。为此,海德格尔提出了“向死而生”。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如果我让死亡进入我的生命,接受它,直面它,就可以摆脱死亡的恐惧和生活的琐碎——那时候我才会自由地成为自己。”诚哉斯言!
展开剩余76%毋庸讳言,死亡问题是哲学的本质问题,也是哲学家们与我们常人不分高低贵贱而直面的最根本的人生问题。正如西蒙·克里切利在《哲学家死亡录》中所说:“哲学家对待死亡的方式赋予了他们以人性,并且也表明,尽管他们的知识水平很高,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像我们其余人一样来面对生活带来的难题。”但如何理解死亡,如何理解哲学事业与死亡的关系,哲学家们表现出非同凡响的识见。作为语文老师,我也在不断建立语文课、哲学与死亡的关系式。柏拉图说:“哲学就是死亡练习。”而“练习”究其本质是思维的训练和情志的考验。将语文课堂上的“死亡主题”教育看作这样的训练也未尝不可以。
但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语文教师,关心死亡实际上还是为了更深刻地去觉解生命。连中国老师在《语文课》中这样说:“语文课核心是干什么?它其实是透过语言文字这个媒介,去觉解生命。”所以,哲学的事业也是探求生命奥妙的事业,阅读哲学经典就是去体悟生命的奥妙并进而觉解生命。
记忆中第一次参加语文课堂大赛,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篇哲学经典——冯友兰先生的《人生的境界》。作为新理学的代表性人物,冯先生的“境界说”在中国哲学界可谓盛极一时。大学时代,我在西方文论课上第一次听老师说起冯友兰的名字,下课后就一股脑冲进图书馆,“扫荡”馆存的冯先生的作品。一套《中国哲学史》,如饥似渴地读了一个星期,真是酣畅淋漓。凭着自己一点掉书袋的功夫和对哲学世界的一往情深,那堂课赢得了评委“华丽而汪洋”的评价。但评委也委婉地指出我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其实评委也是隔靴搔痒,准确地说,应该是上成了哲学课。抛开课型界限不论,我的那堂课本应该是“哲学”与“语文”的一次“二重唱”。只是因为哲学经典的天空气场太过强大,目眩神迷中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实际上是站在语文的大地之上,结果变成了哲学的独唱。但我自信是以最本色的方式致敬了《人生的境界》,致敬了冯友兰先生。
有了这样一堂毁誉参半的课,我决定再有参加课堂大赛的机会,一定要在课堂上奏出一曲哲学与语文的交响乐。因此,当第二次参加语文课堂大赛时,我仍然选择了一篇哲学经典文本。不过,这一次是《逍遥游》,堪称庄子版《人生的境界》,但光芒更加璀璨,因为文本本身就是哲学经典与语文经典的一次秘妙的结合。为了准备这堂课,我把虽已读过但没读透的《庄子》反反复复“嚼”了几个来回,并通读了大量庄子哲学研究的力作。其中印象至深的当数王博的《庄子哲学》和张远山的《庄子奥义》。前者重在庄子精神的体悟,后者重在庄子奥义的抉发,可谓各有千秋。这种看似功利性的阅读其实让我有了一次集中精力直面庄子的机会。于我而言,《庄子》是一座值得不断攀爬的经典珠峰。读《庄子》不仅仅是慧根与智性的考量,更是良知与心性的训练。或许此生并不能登顶这样的山峰,仰望苍穹浩渺,俯瞰万峰苍茫,但不断攀爬其实就是一种切近,而且每一次的切近都会有新的视域与心界。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讲《逍遥游》正是一次对经典的重读与切近。站在《逍遥游》作为语文经典的大地之上,我终于完成了一次凝望《庄子》哲学天空的大胆尝试。
哲学经典的阅读对于一个语文教师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学科阅读,更应该体现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人生阅读。我赞成法国哲学家吕克·费希和克劳德·卡佩里耶二人对哲学一词的看法:“哲学不只关乎道德,也不是宗教信仰,它关注世俗的精神性,所有伟大哲学都毫无例外地在回答什么是好生活的问题时达到。”哲学关乎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生活的建构需要哲学的思考和见识。以赛亚·伯林说:“哲学的太阳逐渐喷射出巨大的燃烧气团,这些气团后来凝成星体,并进而产生了自己的生命。”这如同我们阅读伟大的文学经典一样,其最终目的无非是丰润和深邃我们的人生体验,对哲学经典的阅读可谓殊途同归。
所以,海德格尔把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的诗歌当作哲学经典来阅读和阐释时,毋宁说他是在用诗化哲学的方式体验人生。而我读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艺术作品的本源》《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著作时,对“诗意”“艺术”“语言”这样一些语文教师似乎耳熟能详的概念有了前所未有的智性体验,因为这些概念都被置于哲学的空间内打量、还原与建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我在重新解读诗歌等文学作品时获得了新的视域和体验,更重要的是它让我透过语言的“言说”,祛蔽至于澄明,从而通达生命的本真和根底。
我坚信:真正的文学一定在述说世界的过程中与哲学有着默契的会晤。正如狄尔泰在《哲学与诗人的人生观》中写的:“每一种抒情诗、叙事诗或戏剧诗都把一种特殊的体验突进到反思对其意义的高度。”因此,哲学经典的阅读究其本质,就是对意义世界的探索与追寻。语文教师的根本使命就在于用母语为学生构建起精神世界和人生意义的大厦股票如何申请杠杆,而哲学经典的阅读无疑将会使这座大厦变得沉稳而高深。我以为,哲学经典的阅读理应成为语文教师的另一种使命。
发布于:四川省
